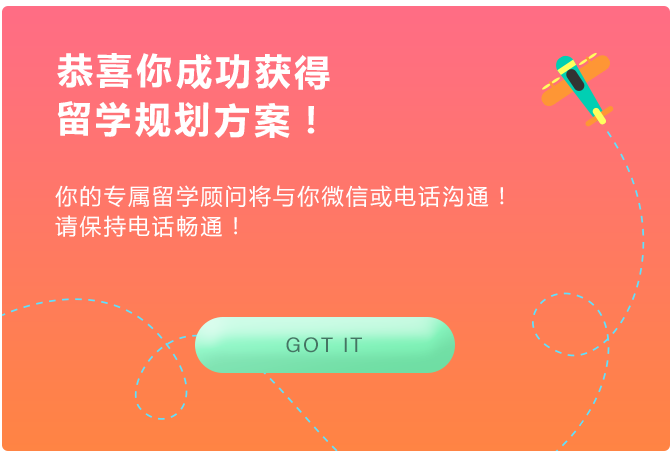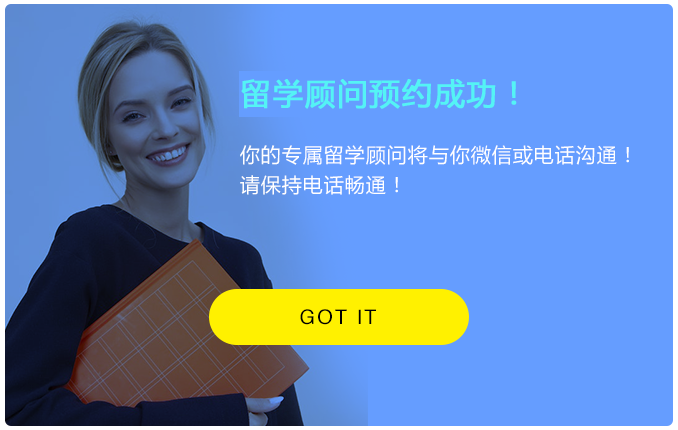一、学科建制:从"民俗学"到"文化人类学"的谱系演变
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制经历了从民俗学(folklore studies)到民族学(ethnology)再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复杂演变,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日本知识界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持续思考。
(一)柳田国男与"一国民俗学"的奠基
柳田国男(1875-1962)被视为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也是日本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思想源头。1910年,柳田成立"乡土研究会",标志着日本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
。他的学术生涯体现了日本文化人类学独特的本土关怀:1909-1910年集中出版《远野物语》《后狩词记》《石神问答》三部开拓之作,1913年与高木敏雄创办《乡土研究》杂志,开启了系统的田野调查传统
。
柳田的民俗学具有鲜明的经世济民特征。面对明治维新后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农村凋敝,他提出民俗学应"阐明各个乡土地区的民众生活怎样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规律,怎样使村落居民幸福地生活"
。他强调,通过文献学无法了解日本的民族性,因为日本文献中只有贵族豪杰的列传,缺乏平民的历史记录,因此必须采取"实地采集资料"的新方法
。
然而,柳田的民俗学也包含深刻的民族主义维度。20世纪30-40年代,他试图通过民俗学重建"国民道德",让国民了解"从前的道德"和"日本人"形成邻村生活形态的艰难,从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萌生"国民的一体感"
。这种"一国民俗学"(一国民俗学)构想,既是对西方人类学殖民倾向的批判——柳田认为欧美人类学者"对被统治者缺乏真正了解,其研究只是西方人对'他者'的表现"
——也埋下了战后日本民俗学"脱世界化"的隐患。
(二)战后转型:从民族学到文化人类学
日本人类学的制度建制始于1884年坪井正五郎等人发起的"人类学之友会",1886年改称"东京人类学会",1893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正式成立人类学讲座
。战前,日本人类学以台湾、朝鲜、南洋群岛等殖民地为主要调查地,与帝国扩张紧密相连。
战后,学科经历了深刻转型。1964年,"日本民族学会"从"民族学协会"中独立,2004年正式更名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
。这一更名不仅是术语的更迭,更标志着研究范式从以"民族"(ethnos)为核心的实体论,转向以"文化"(culture)为核心的象征论与实践论。
学会的成立沿革体现了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双重定位:既坚持异文化研究这一国际人类学的基本方向,又保持与民俗学相结合的本民族文化研究传统
。这种"内外兼修"的学术格局,使日本文化人类学在全球化学术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贡献。
二、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从"乡土"到"都市"的范式转换
田野调查(fieldwork)是日本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方法,其发展轨迹从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延伸至当代的"都市民俗学",经历了从空间到时间、从农村到都市、从静态到动态的范式转换。
(一)柳田范式:乡土调查的伦理与方法
柳田国男确立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鲜明的本土方法论特征:
第一,重访与比较。柳田强调"短期間の滞在を数回繰り返す"(重复进行短期滞留)的调查方式,反对长期单点居住的传统人类学方法
。他认为,通过反复访问不同地点,可以发现民俗事象的变异性与分布规律,建立"重层性"(重層性)的历史理解。
第二,知识人协作。柳田重视与"现地の知識人"(当地知识人)的合作,培养了大量本土调查员(如早川孝太郎),形成"内部人"研究的独特模式
。这种方法既避免了西方人类学的"外部凝视",也产生了表征政治的问题——东京知识分子记录乡村叙事,是否真正代表了乡村民众的声音?
第三,分类体系。柳田建立了精密的民俗资料分类法:物质民俗(住居、服装、食物等)、口头民俗(词汇、谚语、民间故事等)、习俗民俗(精灵、禁忌、迷信等)
。这种分类不仅具有资料整理功能,更体现了将"生活文化"(生活文化)体系化的学术野心。
(二)战后发展:都市民俗学的兴起
日本高度经济增长期(1955-1973)彻底改变了田野调查的社会条件。社会学者加藤秀俊在1957年《中间文化》中指出,日本社会从阶级社会向"大众社会"转变,农村青年对知识分子的相机不再感到新奇,甚至能讨论相机型号
。这种"现代化"进程使传统民俗学的调查对象——"与世隔绝的农民"——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下,都市民俗学应运而生。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将其分为四个类型:
-
在都市发现民俗:将既有民俗事象的调查地点从农村转向都市;
-
都市形成的特有民俗:如都市传说、学校怪谈等新兴口头传承;
-
传统都市中的民俗事象:历史都市(如京都、奈良)中的传统信仰与节庆;
-
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新类型:对"现在"的讲述,如"世间话"(闲聊)。
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支撑仍是柳田的"城乡连续体论",但研究对象已从传承(transmission)转向变容(transformation),从过去(past)转向现在(present)。这种转向使民俗学从"拯救濒临消失的遗产"的危机意识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文化生产的动态过程。
(三)田野伦理的当代反思
日本文化人类学对田野调查伦理的反思尤为深刻。1972年,爱努(Ainu)人权活动家鳩澤佐美夫批评爱努学者和研究者是"害虫",对爱努文化造成破坏
。这一批评促使日本人类学者重新审视田野工作的权力关系。
鶴見良行(1927-1996)代表了新的田野研究方式。作为非学院派的"步行民俗学者",他调查的不再是日本的民众,而是亚洲边境地方的民众,从文化与政治经济问题的角度书写
。他的研究从中心转向周边、从大民族转向小民族、从支配阶层转向普通大众,体现了"柳田国男型国族主义的良心型发展"的国际可能性
。
这种反思在方法论上体现为:
-
从观察到对话:将调查对象视为研究合作者而非信息提供者;
-
从提取到回馈:研究成果向调查社区返还,促进文化自觉;
-
从单一地点到多点民族志:追踪跨地域、跨国的文化流动。
三、跨文化理解:从"一国民俗学"到"世界民俗学"
日本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议题是跨文化理解(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这一议题的理论深化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从文化本质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演变。
(一)柳田的"世界民俗学"构想
柳田国男晚年提出"世界民俗学"(世界民俗学)构想,试图将"一国民俗学"与全球比较研究相结合
。这一构想的背景是柳田对"日本文化论"国际传播的深切关注——他认为日本有大量民俗资料,与新教国家相比具有优势,应该努力做好民俗学以"胜过欧洲"
。
然而,桑山敬己等学者指出,柳田的"世界民俗学"存在根本矛盾:它试图通过"去世界化"(一国主义)来实现"世界化",缺乏真正的对话空间
。柳田对欧美人类学的抗拒,既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身份政治策略(类似于当代印度知识分子的后殖民立场),也限制了日本民俗学与国际学界的深度对话
。
(二)战后的国际化转向
战后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国际化体现在两个维度:
第一,调查地的全球化。战后日本人类学摆脱了殖民地框架,调查范围扩展至东南亚、大洋洲、非洲、南美洲乃至欧美社会
。这种扩展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从"文明vs野蛮"的进化论框架,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框架。
第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日本学者积极吸纳美国文化人类学、法国结构主义、英国社会人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比较研究传统。例如,日本与印尼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文化亲缘关系与独立起源的复杂交织
。
(三)异文化理解的学术实践
日本文化人类学对异文化理解的贡献体现在方法论创新上:
文化相对主义的深化。人类学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存在绝对优劣标准
。这种理念对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通过研究日本敬语的使用,可以理解日本文化中和谐(和)与关系(間柄)的核心价值,而非简单视为"繁文缛节"
。
参与观察的精细化。余光弘教授指出,田野调查"就是学做人,要学会察言观色",不要太早问问题,也不要太容易轻信,必须经过自己的调查再得出结论
。这种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重视,超越了传统实证主义的客观性追求。
跨文化比较的系统化。日本学者发展出精细的比较方法论:同比(相同点比较)、异比(不同点比较)、横向比较(共时截面)、纵向比较(历时断面)、阐发比较(以新视角发现文化价值)等
。这种方法论工具箱使日本文化人类学在东亚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独特优势。
四、当代议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人类学
当代日本文化人类学面临深刻的时代挑战与学科重构。
(一)都市民俗学的深化
福田亚细男指出,当代日本民俗学需要超越"二十世纪民俗学"的框架,直面现代性本身
。都市民俗学不仅研究都市中的传统遗存,更关注都市作为文化生产场域的独特逻辑:信息社会的劳动与情报、全球化的跨文化接触、媒介化的虚拟民族志等新议题
。
这种深化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从"重层性"(历史层累)转向"時間の民俗学"(时间的民俗学)——关注文化事象在现在的生成与流通,而非仅仅追溯其历史起源
。
(二)跨学科合作的拓展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跨文化冲突)难以用单一学科阐释,需要综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医学等多学科知识
。文化人类学因其对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整体把握能力,在解决这些"超领域"问题中具有独特贡献。
特别是在跨文化理解领域,人类学研究为多元文化国际背景下的和谐共存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与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高龄化、移民增加、地方创生等现实议题紧密相关。
(三)国际合作与知识生产
日本文化人类学正从"为自身利益研究他者"转向"通过国际合作进行跨文化研究"
。这种转向体现在:
-
亚洲田野的协作:日本学者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研究者开展联合调查,如福田亚细男1980年代至2010年引领的六期中日民俗学联合田野调查;
-
方法论对话:将中国民俗学的"采风"传统与日本民俗学的"乡土研究"方法相互参照,探索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
-
学术话语的双向流动:既将日本研究成果英文化(如Japanese Review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也将海外日本研究引入本土讨论(如对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持续批判性反思)。
五、方法论特色: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贡献
总结而言,日本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形成了区别于欧美传统的独特贡献:
(一)"内外兼备"的研究格局
日本文化人类学坚持异文化研究与本民族文化研究并重的"双轨制"
。这种格局既避免了欧美人类学过度依赖"远方他者"的倾向,也克服了本土研究可能陷入的民族主义陷阱。通过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不断穿梭(shuttle),研究者保持了敏锐的文化自觉。
(二)"重层性"的历史视野
柳田国男开创的重层性(重層性)概念,强调文化事象的历史层累与空间分布的相互交织。这种方法不仅关注文化的共时结构,更追溯其历时演变,形成"从过去理解现在"的独特时间观
。
(三)"经世济民"的学术伦理
日本文化人类学始终强调学问的社会实践性。无论是柳田国男对农村困境的关怀,还是当代学者对少子高龄化、地方创生等议题的参与,都体现了"学问不是小圈子的艺术趣味,而是应该对社会的人们有帮助"的理念
。这种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取向,使学术研究与公民社会形成了紧密互动。
(四)"批评与对话"的跨文化立场
日本文化人类学在批判西方学术霸权与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桑山敬己指出,日本人类学需要警惕"学术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同时也要反思柳田国男"一国主义"的局限性,在国际合作中重建对话空间
。
结语
日本文化人类学从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出发,经历了战后国际化、都市民俗学转型、全球化时代的跨学科拓展,形成了田野调查精密化、跨文化理解深度化、学术伦理实践化的学科特色。
其独特价值在于:在东西方学术传统的交汇点上,既保持了本土文化研究的细腻与深度,又获得了国际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与方法论严谨;既坚守了经世济民的学术传统,又展开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对于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而言,日本同行的经验提示我们:田野调查不仅是资料收集技术,更是文化理解的艺术;跨文化比较不仅是找出异同,更是建立对话;学术实践不仅是知识生产,更是社会参与。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代,日本文化人类学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如何超越"日本特殊性"的话语框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重新诠释"乡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既是对柳田国男"世界民俗学"构想的历史回应,也是文化人类学作为"理解之学问"的当代使命。
 日本
日本
 韩国
韩国
 英国
英国
 新加坡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398
398
 2026-02-04 13:25
2026-02-04 13:25